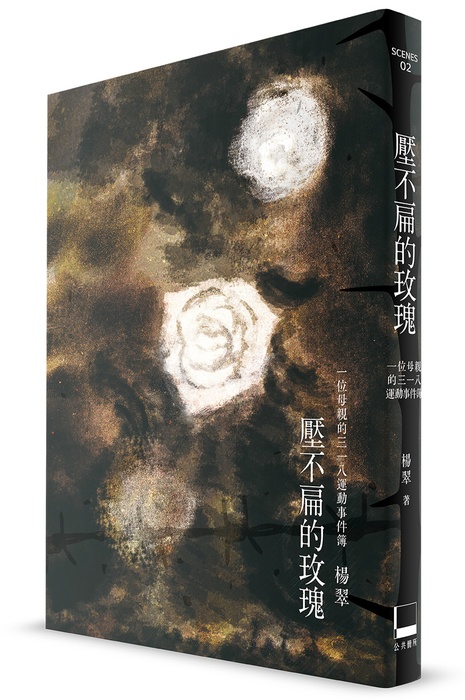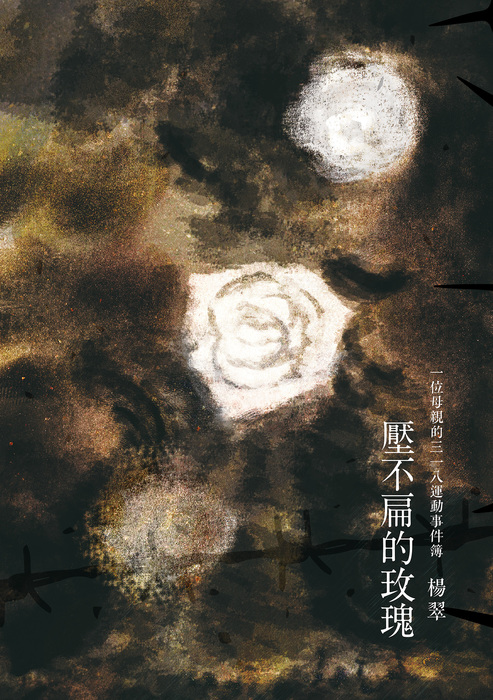序
推薦序
挺起長矛衝向風車 廖玉蕙
秋日裡,捧讀這樣的一卷文章,心情驀地激動了起來。
經歷幾個月了,那場驚天動地的太陽花運動,恍惚迷離,像一場夢,似幻還真;而藉由楊翠和魏揚這些倉皇揪心的文字,它彷彿又迤迤邐邐回來了,夾帶著批判和反省。書裡記錄了運動前後的種種,回顧與瞻望,投入與逸出;小自對貓狗的疼惜,大至對臺灣前途的關心,楊翠以母親的情懷,絮絮叨叨,不但和兒子魏揚對話,也和整個體制對話,甚至跟自己對話。
回想我跟楊翠首次見面,距今已是四十多個年頭了。當時,我在《幼獅文藝》打工,奉主編之命前往東海花園採訪楊翠的阿公楊逵先生,在大鄧伯花迎風搖曳的花架下,當時猶然稚齡的楊翠就睜著一雙大眼坐在小板凳上靜靜聆聽,我後來常戲稱當時的楊翠「還是個流著鼻涕的小女孩」。那次去採訪了楊逵先生後,洋洋灑灑寫完採訪稿,卻基於某些禁忌,有疑慮的部分都被主編刪削殆盡,讓我感到萬分挫折,也深覺對不起楊老先生一整個午後的懇談。於是,在寄奉刊登了採訪稿的雜誌的同時,我給他老人家寫了封信,深致歉意。
在那之後的二十多年,我和楊翠再度邂逅,這回,輪到她為臺中縣文化局委託案來採訪身為臺中縣籍作家的我。詭異的是,這次楊翠特意北上到寒舍的採訪,竟然在返回臺中的途中,發現錄音帶完全空白,一句也沒錄到。這回,換成楊翠用電話跟我致歉,這真是「一報還一報」了,人生緣會真是奇特。
當時,在給楊逵先生的致歉信裡,我寫了:「為了某種不得已的因素而無法原文刊登,希望多加擔待。下次回臺中時,再當面請罪」之類的話,沒料到這封信連同其他的幾封給別的作家的信全被在警總任職的一位瘂弦主編的學生影印了,並在信中某些敏感字句旁塗抹了鮮艷的紅線寄回社裡﹔他警告主編要約束我這位「天真」的編輯,不得狂言妄語,否則難免牢獄之災,這是我首次見識了警總的文網之密及白色恐怖的可怕。
其後,我離開雜誌社,進到軍校教書。那年,我邊教書,邊念博士班。一日,在紅學大師潘重規教授的課後,大夥兒打開電視機,電視上出現立委跳上議事桌扯掉麥克風的畫面,我們看了驚心動魄,潘教授卻神情怡然地說:「若要讓既得利益者釋出利益或權力,沒有用非常的手段是萬萬行不通的!」我瞿然大驚,心裡恍似有了那麼點什麼東西被啟發了!
過沒多久,萬年國代成為歷史;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國會全面改選;釋放政治犯……在反對運動者的努力與全民的期待下,一樁樁、一件件的保守或不公不義都日趨合理,我當初的疑懼才逐漸冰釋。傳統的勢力永遠存在,看似牢不可拔,卻也輸給了改革的毅力;而在前人的努力下得到的成果,似乎並不為所有人所記憶,但走過歲月的我是記得的。我曾在軍中這個巨大的謊言機器裡待過十九年,脫身出來後,向前瞻望並回頭審視,除了欽敬那些先知先覺者,慚愧自己的後知後覺外,也慶幸我還沒有不知不覺,但我仍刻意和所謂的反對運動保持距離。
又過了幾年,因為同是臺中老鄉,楊翠還是我臺中女中的學妹,我們略略有了交往,但真正相處的時間並不多,我只覺她天生一種小女子的嬌憨,非常浪漫可愛。後來,我們有機會一起到緬甸觀光,日遊夜談,彼此才有更多的了解。當時,楊翠還帶著神情略顯恍惚的母親同往,回程時,我們比鄰而坐,有了機會深談,也才了然白色恐怖的陰影如影隨形,身為楊逵家族的成員背後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酸。
可能是涉世日深,對人世的理解越甚,也可能是像楊翠這樣的朋友的潛移默化,我開始發現我以前的生活過得實在糊塗,也逐漸憬悟:文學裡的文字斟酌、情節鋪陳、結構設計都只是其次;不管是閱讀或寫作,都應該是用來幫助我們建構自己的人生,它是要讓生活變容易的一種思考過程。我想起曾經看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祕魯的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裡說的幾段話:
編造故事的早熟才能,即作家抱負的起點。它的起源是什麼呢?我想答案是:反抗精神。……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應該堅決、徹底和深入,永遠保持這樣的行動熱情——如同唐吉軻德那樣挺起長矛衝向風車。……優秀文學鼓勵這種對現實世界的焦慮,在特定的環境裡也可能轉化為面對政權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
經過大半生的努力,我過著退休後的好日子,有屋、有車、有子、有孫,但我也知道,若沒有努力督責,不但我的小孫女將來日子不好過,我今生的努力也許也將泡湯。
無論如何,如今身為職業作家的我,不想只躲在書房裡用著華麗的辭藻設想或編造人生,或慶幸終身俸保障了我的餘生;我得用腳站立在真實的生活裡,體切地感受吃苦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並將心比心。只有幸福的人也一起下去努力,才能得到長久的幸福。而不管文學或文學教育都不止於文字或教室內,我於是開始跟著吳晟撰文反國光石化的興建;跟著楊翠參與了我人生當中的第一場反核遊行,接著是華光社區的拆遷的抗議,再來是帶著小孫女為洪仲丘事件走上凱道。
當太陽花運動展開時,外頭的世界已整個變得沸沸揚揚的,課堂上,師生同等張惶;課堂外,在濟南路、在凱道上、在青島東路上,我們在擁擠的人潮中師生對視,心領神會反倒都覺安心。我鼓起勇氣應邀走上濟南路的講台慷慨陳辭,不知怎的,竟語帶哽咽。
走路回家時,穿行臺北街頭,紹興南路安靜無聲,但車流的燈火閃爍,我默默地走著,感受巨大的寂寞。那些我當年教過的軍校學生,我如此珍視與他們的相遇緣會,那曾經是我被禁錮的青壯靈魂最寄予厚望的純真學子,如今或退休或在職,卻奇異地因想法背道而言語扞格,師生的距離在臉書上竟越來越遠了。我在臉書上、在報紙上看到他們不斷徵引美國人講究秩序的反對運動,但似乎都刻意遺忘早年美國人在社會議題的抗爭的激烈。當年反越戰時,那些flower children 拿一朵花在槍桿子前的照片、舊金山同志的石牆運動……難道都是手拉手溫柔的抗議?還有一些人總是歌頌美國可以恣意逮捕、任意毆打的警察權,但似乎刻意迴避威權的解體、平等的獲得,都是因為堅定的抗爭才得來,絕非警察權的過度動用。
我在臉書上苦口婆心反駁:十九世紀美國南方虐待甚至虐死黑人是合法的,因為黑人是私有財產,但合法與非法,還得回歸有沒有正當性,不是只要合法就行了,法律得隨著時代的輪軸運轉改變。電影《自由大道》裡的同志哈維,《自由之心》中的索羅門的血淚創傷……電影具體呈現了時代的痛;我們在電影院裡為這些真人真事改編的人生流下同情的眼淚,卻在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世界後,強調警察打人的必須,這不是太荒謬了?
太陽花運動落幕了,我還在不停地思考,要怎樣做才能讓他們明白老師的苦心?我在楊翠這本書裡找到了部分答案,看似溫柔的楊翠,其實內裡剛強;迷糊行為不斷的她,論述意外地井然,且深具說服力。而說到魏揚這位可畏的後生,經過許多的努力和這一場充滿刺激性的洗禮後,似乎已逐漸將自己鍛鍊成一位俯仰無愧的冷靜領導人才。下回,我見到他時,看來只能對他豎起大拇指坦承:「一代不如一代,我們那一代的行動力真的遠遠不如你們這一代,請繼續加油。」
自序
謝謝你曾經那樣守護我 楊翠
你可以壓扁玫瑰,但無法延遲春天。--聶魯達
我蹲下去一看,看到了被水泥塊壓在底下的一棵玫瑰花。被壓得密密的,竟從小小的縫間抽出一些芽,還長出一個拇指大的花苞。--楊逵
這本書,容我這麼說,是一個告別。告別這個春天的繁花麗景,告別一個時代的終了,或者,也是告別過往自身,告別某種母子關係。做為楊逵最疼愛的孫女,終須從他的光照與暗影中脫身,做為母親,也終要放手。
歷經幾個月的苦思,我接受青年編輯夥伴的建議,挪用楊逵小說〈壓不扁的玫瑰〉,做為書名,魏貽君聽後,直說不妥,我可以理解,因為沒創意又太方便。但是,這個書名,做為一個多重隱喻,卻很能詮釋我目前的生命狀態。
當潮紅熱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昔日少女跌撞步入更年期,才真正感知到,紅顏已老,孩子已經長大,而我必須告別故舊,才能走上新的人生。「壓不扁的玫瑰」,當然有它固定的意義,指涉被殖民者、弱勢者的不服從與抵抗,符合三一八以來的公民運動風潮。然而,「壓不扁的玫瑰」,也被解讀為一則屬於楊逵家族的精神符碼,表徵著這個家族的抵抗、壓抑、受苦、奮起、反抗的世代承繼。這種家族承繼的社會想像,過去五十年,成為我無法揚棄的生命重量,現在,它被加諸在魏揚身上。
血的承繼觀,其實是一種思想暴力。如果一個生命主體勇敢挺身做了什麼,不是因為家族的血脈召喚,而是他自身的覺醒與勇敢;他要先是自己,才能以他的生命實踐,成為家族的一則故事。
因此,《壓不扁的玫瑰》必須是一個告別,要先告別,我們才能真正回家。楊逵最疼愛的孫女,挪用阿公書名,是禮敬,是告別,也是為了回家。
逝水,不只是年華
返回台中舊居,整理舊物。黃昏,夕陽穿過櫛比如林的大水塔,從西方窗口斜映進來,我身旁散落著各式各樣的時間標本,有三十年前蒐集的樹木種子,有孩子的母親節賀卡,有學生的謝卡禮物,有二十年前好友的信件,有自己的心情塗鴉,有寫給老公的絕情信,有孩子傷痕累累的聯絡簿,還有他從開始拿筆到國中的大量畫作。
燦麗夕陽打光,這些舊物散發著詭異的嫵媚感,彷彿如新。天色很快暗下後,我一直賴著,沒去點燈。物件堆疊,老舊時間所積累的塵埃飛揚,偶爾,一隻蠹蟲從殘破的書頁中爬行出來,伸著懶腰,一見我,飛快逃逸。我有如置身廢墟中,一件件檢視、分類、丟棄、裝箱,等到四面都是夜色,眼前起了黑霧,才起身點燈。
有些餓,但一個人的時候,什麼都不想吃。撐到九點多,終於決定到東海別墅逛逛,吃點東西。入夜,在大肚山獨行,突然一陣傷感。一家人曾經在這座山頭生活過二十年的生命痕跡,竟然淺淡如斯,許多地點,看似擱淺著舊日時光,仔細辨識,卻是物非人非。我抓不到最適當的回憶焦距。
最近特別想念那些日子。一家人,說說笑笑,吵吵鬧鬧,或是冷戰不語,穿過山城街巷。
跨過中年以後,感到生命有如各種廢墟。這些日子想起很多,有一些情景,如潮水退位,是永遠不會復返了。逝水,不只是年華,還有那些暖熱體溫,以及可以測量彼此體溫的依憑。
純真年代
他一直是個貼心的孩子,溫柔、心軟、好商量,有時我覺得是他在守護我。那些年,他跟著我們流徙在故鄉大肚山,居無定所。一九九一年歲末,我們決意歸返台中,在大肚鄉中沙路,自強市場旁,租賃一處眷村的二層樓房,無業,沒有收入,帶著一個三歲小孩,每月等一張稿費匯票,常常青黃不接,沒有明天的菜錢。
他從三歲就在這裡長大,小小的身體,大大的頭顱,頑皮靈動,卻又難以想像的好商量。市場裡到處是誘惑,詢問幾次後,他知道我有時青黃不接,沒錢買,在玩具攤前停下腳步時,總是背著手,蹲下身說,我看看就好,然後專注凝視地面上各式華美玩具,過了些時,起身說,好,我看好了我們走吧。那時多好,攜著他的手走逛,世界總是很美麗,沒有菜錢的日子,熬一熬就會過去。
他第一天上幼稚園時,是個週末,我們憂心他把學校給拆了,一上午都忐忑不安,提早去接他,偷偷躲在門外張望,像看恐怖片一般。卻沒想,他好乖好乖地坐著聽故事,小臉仰起,聽得入神,嘴巴微張,還帶著一抹微笑。
那時我總是可以準確猜中他在學校做過什麼、發生什麼,以一個推理小說迷的基本功力而已。被我說中時,他驚問你怎麼知道,我就說,媽媽大眼睛有看到啊。那時他真的相信,每每接他下課,閒談說話間,他就瞪大眼睛問,媽媽,你是大眼睛有看到嗎?然後母子就笑成一團,我想那時候他很崇拜我吧,媽媽的大眼睛真神奇,穿山越水,什麼都看得見。
幼稚園老師好愛他,愛他頑皮,愛他天賦才情。他最先表現的才氣是畫畫,好像《阿羅有枝彩色筆》裡的阿羅,一本書、一疊紙、一枝筆,行走天涯。他把所有書本紙頁牆壁地面都當成畫紙,豪邁揮灑,台中舊家裝修前,樓梯牆面都是他的壁畫。
他有說故事的天份,從幼稚園時期就愛表演說故事,一群大人圍坐,微笑看他比手劃腳,眼神放光。他好有自信,畫畫、說故事,是他給我們的饗宴,鬧脾氣時,他就放話說,那我不畫畫給你看了,也不說故事給你聽了,我們向他求饒,拜託拜託啦,他就滿足地揚起臉,咧嘴燦笑,說,那好吧,有點驕傲。
謝謝你曾經守護我
一九九三年初,我們搬進新的賃居處所,也在大肚鄉中沙路,臥室是一個沒有窗戶的黝暗空間。
初春的某一日,我在夜裡流產了,未滿三個月的胎兒,腹中散形。清晨在暈眩中醒來,我發現自己躺在一灘濡濕中,鮮血染紅整條墊被。
那日,魏貽君一早就到清華上課,他當時在唸碩士班,剛過四歲的魏揚去上幼稚園。撐到中午,我穿戴妥當,獨自靜靜等候他的娃娃車返家,告訴他,媽媽不舒服,我們要去醫院。然後母子倆去搭公車,一路晃到榮總,我緊緊抓著他的手,穿過地下道,走進急診室。護士見我,眼神狐疑,似乎覺得你都還能照顧小孩,不讓我掛急診,說急診室滿了,我說可是我的頭真的好暈啊,她說那就先量血壓再說吧。
低壓五十,高壓八十,過低,護士立刻聯絡醫師。我躺在急診室一處簡陋的病房裡,醫師來了,問了兩句,沒有任何前置作業,隨即以雙手穿入內診,我忍著一股穿透擠壓的粗暴力量,頃刻間,他抓出變形的胎兒,然後棄置一旁的垃圾桶,說,可以了,明天再來掛門診,照個超音波,看看有沒有拿乾淨。
醫師走了,我眩暈起身,偷瞄垃圾桶一眼,血肉模糊。醫師動作之間,我空慌恍神,卻清楚記得魏揚坐在隔壁病床上,隔著拉上的布簾,吃著餅乾,ㄎㄎㄎㄎ,從餅乾聲音的間隙中,他憂心地呼喚著:「媽媽,你還好嗎?媽媽,你怎麼了?」清脆的童音,夾帶著隱忍的哭聲。
直到現在,那個簡陋的急診病房,醫師粗暴伸入的雙手,都還是我的深沉夢魘。但是,布簾彼方的魏揚,卻以他的童音,他隱忍的憂心,溫暖地守護了我。
青春就要起行
然後,進入小學,我們的世界一度變異。那時我最害怕的就是看聯絡簿,總是假裝遺忘,卻如大石懸心。他也是。聯絡簿是黃色,母子倆弄到最後,連看到紅綠燈的黃燈都心驚肉跳;我怕他想到聯絡簿沒簽,打開書包掏出來給我,簿上又是一片慘烈風景;他怕我想到聯絡簿沒簽,吩咐他打開書包掏出來給我,車上將是一片寒冷空氣。母子天天有如上演安靜諜戰,或者其實是相互推諉。
然後,感謝他遇到伯樂,恢復幼稚園的自信。此後,他創作、閱讀、畫畫、研究,堅定找到自己的道路。上了清華大學後,他好喜歡他的老師們,從大一開始,假日返家,就是他的學習分享日,他還發下豪語說,最大的心願就是回到清華,和老師成為同事,成為夥伴。許多夜晚,一家徹夜歡談,有時女性主義,有時文學歷史,有時藝術戲劇,有時哲學社會學,他在白板上,又畫又寫,神情飛揚,一如童幼時期,他說著故事,我們仰頭,微笑看他,說得真好啊,魏老師。
這是他以寫作和學術為志的年代,燃燒著青春的光色。童幼時期,他想當科學家,立志尋找全世界的恐龍骨頭,蓋一座免費參觀的博物館,我問他那你要靠什麼營生,他說我會去向熱愛恐龍的有錢人募款。我真是佩服他的浪漫和勇氣。
無論是蓋恐龍博物館,或是返回母校當老師的教學夥伴,他慢慢為自己整闢一條路,一個未來,青春就要起行。
春天那場動地歌吟
青春就要起行。然而,因為春天那場動地歌吟,青春的前路,漫漫難行。
其實從去年七月就開始。那時他決定投身青年反服貿運動,行前給我寫了臉書私訊,告知將有一場行動,他擔任總指揮,最後的結果,就是被以「首謀」論處。一封家書,一種覺悟,覺悟此後必將風風雨雨。
三二四在北院等候聲押庭時,他的老師姚人多全日守候。我知道魏揚一定不曾告訴他,關於他們在課堂上給他的感動,以及他想成為老師夥伴的豪夢。他很會說故事,但不擅表達情感。有夢最美,我感謝這些老師為他埋下夢田種子。但是,在那個未知前路的夜晚,我不知道,也不曾去想,這個青年的簡單素樸夢願,是否得以實現。
晚春,這場運動,以「出關播種」的宣誓結束。這場運動中的青年,在「出關播種」後,卻隨即面對各種崩毀,組織、同志、生活、身體、學業、友情、愛情、親情,全都殘破不堪。正如許多父母把自己未竟的希望、未完的志業,全都堆放在孩子身上一般,這個社會集體把他們的夢想,都寄放在這些太陽花青年身上,不願看見他們爭吵,不想聽見他們哀號,不允許他們沮喪,也不讓他們休息。
這場春天裡的動地歌吟,恍若發生在龍宮的虛幻夢景,太陽花青年,出關之後,有如浦島太郎掀開寶盒,瞬間白髮,大家都老去了。
我親眼見證他的蒼老,我知道他的青春終了。我遠遠望著,心痛不忍,又怨怪他將組織擺放首位,選擇與同志的喜怒哀樂、理想與幻滅糾纏,弄得自己牽藤扯葛,滿身傷痕,甚至讓親情成為不存在的選項,從擱延,到擱置,終而擱棄。
我們一年見不到幾次面,他總是匆匆來去。我仍然「大眼睛有看到」,但第一次,我憂心自己失去他了,那個憨直卻又敏感,溫柔卻又作怪,才華洋溢卻又疏懶成性,專注細心卻又大而化之的孩子,現在心裡有一個角落,堆放一些心靈雜物,生命陷入暗黑苦境,我就算「大眼睛有看到」,也無能為力。
我知道必須放手,但卻無法放心,總是惦記著,就像所有天下母親。
感謝你們,以閱讀溫暖我
從春天到夏天,那三、四個月,是我人生的一段歧路。三一八運動中,我有如一個躁鬱症患者,每日釘在電腦前,在FB的街巷中穿行,迷路、狂亂、憂心、憤怒,我自己也不斷在FB的虛擬時空中嘔吐,排泄現實中堆積的穢物。寫著寫著,就寫出超過十萬字的字語,這本書就是我的病歷表。
這本書能夠問世,我要感謝年輕的編輯夥伴們,如果沒有他們的邀約,這些字語,只是混亂的電腦檔案,必將成為另一疊時間遺物。我對出書,一向沒有慾望,累積的作品不少,出上五、六本書不成問題,好友吳晟、廖玉蕙、路寒袖、應鳳凰,都一再激勵我,但我疏懶成性,所有字語,都成舊檔老鬼,葬身電腦。
感謝編輯夥伴的耐心守候,在太陽花青年崩毀後,我也曾經陷入困局,生命步履蹣跚,很有些想放棄了。青年們沒有催促,只是安靜、溫柔,卻又執著地看顧著我,守候這本書的產出。
這些年,我的寫作比較傾向於自剖式,習慣誠實暴露自己的軟弱、疲憊、憂鬱、困頓。書寫時,一如置身診療室,算是一種自我療癒吧。透過書寫治療,洗滌自我,吞嚥暗影,吐出陽光,在現實中,換來更多生命能量。
謝謝李喬老師、平路、玉蕙和貽君,你們的文字,有如打光,為我註解了生命中最困難的一段日月,我無以回報,只能默默收納儲放。感謝所有曾經以閱讀溫暖過我的朋友,這些在FB上的囈語,因為有你們的溫情暖意,就成了有意義的靈魂產聲。
然後,序文似乎總也寫不完,我捨不得告別,但知道終於還是要放手放心。感謝你成為我的孩子,感謝你曾經以你的童心、憂慮守護過我,以你的天真、青春、夢想、實踐感動過我,你長成大人的時候,我將已經老去,但我還會默記,那年春天有些繁麗,有些風雨,但你做得很好,母親從來沒有失望過。
內容連載
2014/3/25
三二四,漫長的一日
清晨,仍然守在電腦前,擔心有變,擔心魏揚在警局裡,被陰著打,如一九八八年五二○事件時,魏貽君在城中分局(中正一分局前身)所見證的那般,在警局裡打得更嚴重,更毫無顧忌,更頭破血流。直到飛機航班時間將近,連衣服也沒換,來不及梳洗,披頭散髮就衝出門。上飛機前,打了電話給臺中的妹妹,告知她魏揚被抓了,儘可能瞞著爸爸媽媽,別讓老人家知道,怕他們憂心。
九時許,才剛走進機場大廳,媒體記者就堵在前方。好不容易脫身,搭計程車到延壽路的保安總隊,更大一票記者守候著,我善意地回應了他們那些其實我根本無法回應的問題。現在什麼情況,我根本都不瞭解啊。但由於魏揚被捕,早在我們意料之中,我沒有歇斯底里,也沒有方寸大亂,自然、清醒、冷靜地面對媒體。
進入保總,終於見到魏揚。他看起來很疲倦,但氣色還好,神情穩定,一見我,淺淺笑了,先是說抱歉,讓你們擔心了,又說,千萬不要讓兩邊的阿公阿嬤知道,怕老人家擔心,然後憂慮地問我和律師,聽說現場有人死亡,真的嗎?我們回說沒有,苦勞網等許多消息平臺,都有查明,並無此事,他的眉宇與肩膀,終於放鬆下來。我問他,有被打嗎?身上有傷嗎?他說,被打了,警棍敲頭,翻開雙手背部,因為抵禦鎮暴警察的盾牌攻勢,布滿傷痕,胸腹間也有一片瘀傷,還有,他說,現在知道了,原來手銬這麼緊,這麼痛。
見他情況還好,心情平靜,知道他會勇敢承擔從三二三晚上八點多拿起麥克風那一刻起的司法指控。律師說他要開始接受偵訊了,我便離開保總。女兒來電,說想去看哥哥,我告訴她,哥哥正在接受偵訊,中午過後,應該會有結果,於是我們相約,在東區見面吃飯,等候哥哥的消息。
這一個午后,我和女兒,見證了媒體的無孔不入。媒體的評價,滲進人們的耳朵眼睛,又從人們的嘴巴,原封不動吐出。不是都說臺灣媒體是亂源嗎?民眾一張嘴接一張嘴,既輕信亂源,又傳播亂源。我們走在東區,簡直被嚇到,幾乎不敢行走。
四面八方都在罵魏揚。走在路上,迎面走來的,從背後過來的,捷運的手扶梯,往下走的,往上走的,同聲一氣,都在罵魏揚,罵他腦殘鷹派豬頭白癡無腦,罵他破壞美好的學運,咒他該去坐牢,最好被判重刑。
母女倆走了好久,四面八方,話語網羅,不知該到哪裡去,不時還有人回頭,多看我一眼。可以想像,一早就被媒體包圍,「首謀」的母親也已曝光,我也是他們咬牙切齒的對象。
走來走去,無處可去,無路可走。後來選了麥當勞,心想這裡人多,聲音嘈雜,母女倆至少可以自在一點,說上幾句話。誰知道,麥當勞裡,前後左右,也都在談論行政院事件的「首謀」。當真無處可去。一個輿論如潮、萬箭穿心的概念。我這才真的開始擔心起來,照這樣下去,魏揚日後連走在路上,都艱險萬分啊。
過午,魏揚的老師,我的舊友,清華社會所姚人多老師來電,說他上午已到過保總,但無法見到人,我們相約等一下保總見。不久,捷運上,接到魏揚電話,說他被檢察官指控六大罪狀,聲押禁見,電話告知完畢後,我們就見不了他,也無法再聯繫了,接下來應該會移送臺北地院,等候聲押庭。
聲押禁見,學運史上首例。竟然還禁見,比對付殺人嫌犯還誇張。母女有些六神無主,這下該怎麼辦?後來決定,如果真被羈押,魏揚總要有替換衣物,昨晚他帶到立法院,準備長期抗戰的那一大包衣服,早就扔在行政院現場,不知所蹤了,母女決定去幫哥哥買一些衣服。
在北院的漫長等待,難以一言道盡。過午抵達北院,八點半才開羈押庭,直到翻過午夜十二點半,才終於等到「無保請回」的裁定。而魏揚凌晨四點多就被捕,議場決策核心直到下午四點,才開聲援記者會,沉默近十二個鐘頭,看來是有過一些複雜的折衝過程與政治考量。倒是在北院時,陳板、姚人多等好友,以及魏揚擔任TA 的陳明祺老師,全程陪伴,更有許多好友,紛紛來探、來電、來訊,感謝大家的溫情,支持我冷靜面對一切可能的結局。
無保請回,是正義的裁定。檢察官所提出的「六大罪狀」,都是發生在七點半左右,屬於首波攻占行政院的行動,當時魏揚明明就在客運車上,時空不在場,當然無法成立。我不解,檢察官為何如此不用功,既要指控他,為何以他有明顯不在場證明的時點與事件,而不是以八點多之後他來到現場的指揮行動?
三二五凌晨十二點半,魏揚微笑步出北院押房,為事件劃下第一階段休止符。那包本來想遞進羈押房給他換洗的衣物,還拎在我手上。記者會上,魏揚的發言,簡潔清晰,鏗鏘有力,他更清楚地說:「我負法律責任,馬英九須負歷史責任。行政院衝突的每一滴血,都必須算在現場警察最高指揮官與馬英九總統頭上。」
他走出的那一刻,突然覺得好倦了。我的發言,顯得有些話語慌亂。只是不必羈押而已,未來的法律程序,還很漫長,遠比這一日更漫長,我知道。謝謝大家的各種陪伴,晚安。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祖孫的跨時空經驗
魏揚來電,聲音清朗,問說是否還有人騷擾家裡,我說沒了。
他笑笑說,關於媒體那些「崩潰大哭」、「民進黨青年軍」什麼的,他並不在意。他開玩笑又說:「其實,我最在意的,是網友說,所有好基因都給了妹妹。嗚嗚嗚,好像我長得其貌不揚,都沒人問我的服裝品牌!」
然後母子倆在電話中哈哈大笑。三三○臺北見。
自嘲,是面對逆境的好方法。很歡喜他能如此平靜沉穩。知識分子,為所當為,橫眉冷對千夫指,他能如此,也就放心。
不過,後來想起,他因北院警察的一句「辛苦了加油」而落淚,與一九四九年楊逵的牢獄經驗,竟然有些相似。曾祖與曾孫,跨時空經驗互涉,頗為有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楊逵因「和平宣言案」被捕,其後被判十二年徒刑。在臺中被逮捕後,先押送臺北保安局,在臺北監獄、警務處陽明山招待所、軍法處、情報局等處,轉來轉去,幾個不同的軍警單位,輪流疲勞審訊,要讓他供出「共犯」。
楊逵後來回憶,審訊過程中,曾從國府陣營得到一些意外的溫暖。在警務處陽明山招待所,警備總部的陪審米少校(未仔),曾偷偷稱讚他:「你有印度甘地的風格。」這位米上校,後來也被國民黨以「洩露情報」罪名逮捕,關在保密局,還託獄友傳話,遇見楊逵時,向他問好,並說他自己即將被槍斃。
另一次,則是來自軍法處的衛兵。楊逵入獄後,妻子葉陶也一度入獄,關在軍法處,四個多月,兩棟牢房隔著一片空地,有一名衛兵,不僅特別關照楊逵,還設法讓夫妻可以見面說話。楊逵回憶說:「一位看守衛兵對我十分客氣,普通喊犯人時是叫號碼的,他卻叫我楊先生。此外犯人每天早上只有一杯漱口水洗臉,前後僅兩、三分鐘,不能洗澡。可是在下午沒有人管時,他會打開門叫我去浴室洗澡半個小時。待我洗完,他就開門讓我去葉陶那邊講話;倘若有別人來,他就敲響鑰匙警告,我趕快跑回自己的牢房。我至今仍不瞭解為什麼這位衛兵對我特別好,是不是上面有人叫他這麼做?」
楊逵輾轉在各個軍警單位,接受疲勞審訊,以沉穩、謹慎、堅毅的個性,以及最後的覺悟,度過許多考驗,並且堅持不咬出任何在一陽農園出入的青年及友人,同時還在敵隊陣營中不斷感受溫暖,這些回憶,彰顯出楊逵「正面思考」的性格。
果然,最後,「和平宣言案」僅兩人被判徒刑,白色恐怖時期動輒牽連數十人,一案兩人,是少見的案例。其實,最初逮捕很多人,包括《新生報》副刊「橋」的主編歌雷、《新生報》臺中地區負責人鍾平山,《力行報》則從社長到工友都被捕。楊逵判斷:「抓這麼多人,可能是想看看我們與師範學院和《力行報》有無組織關係。」
經過持續幾天的疲勞審問,無法認定組織關係,被捕者逐漸被釋回,其後僅鍾平山因贊成寫〈和平宣言〉被判十年,楊逵則以「為匪宣傳」罪名判刑十二年。
期許魏揚以此自勉。理性選擇、積極行動、勇敢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