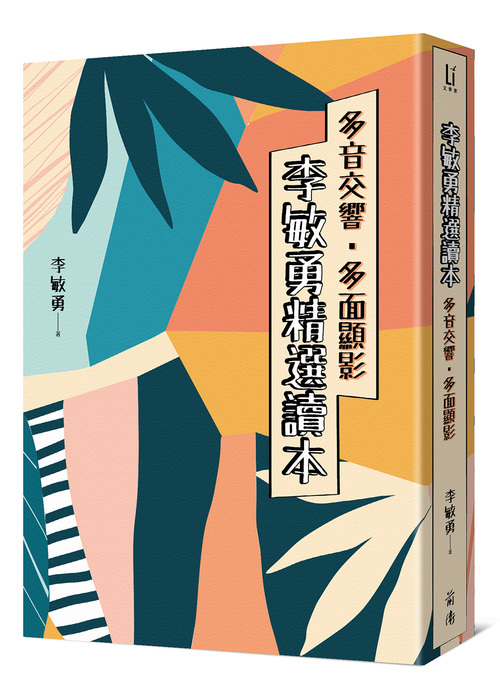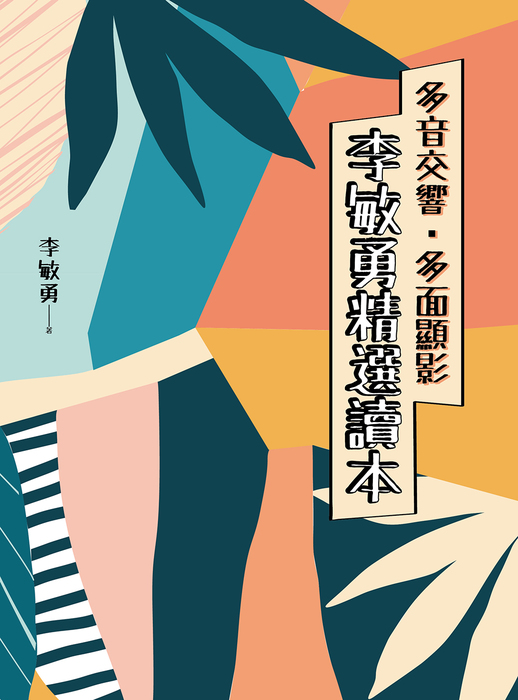序
詩之志,文學心
我的第一本書《雲的語言》出版於一九六九年,距今二○一九年,已五十年半世紀。而我也自人生的青春、走過朱夏、白秋,走向玄冬了。半世紀是人生的長時間,世界從二十世紀走入二十一世紀,從美、蘇帶領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陣營的極權社會主義國家對抗的冷戰時期,走入全球化以貿易競爭競奪的時代。台灣則從黨國專制戒嚴走向民主化奠基,卻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挾走資化的帝國形貌威脅。
出版第一本書,一本收錄詩和散文、我的青春過敏性煩惱的篇章後,我才真正走上詩人之路。一九七○年代,留下《鎮魂歌》和《野生思考》兩本詩集,以反戰和政治違逆的主題,成為一個戰後世代,亦即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精神史見證。一九八○年代,詩集《戒嚴風景》更直指黨國體制下的現實。這是我詩的原型,是在《笠》的詩人學校得到啟諭、經過洗禮後的面向。這三本詩集,以《暗房》這本詩選較早呈現。
戰後性常常是我省思的課題,以二戰為座標,意味著戰敗國和戰勝國的文化省思,對於詩的動向有更血肉化的凝視。我在《笠》的詩人學校和世界詩的詩人學校,開拓自己的詩視野。從戰敗國的詩人作品:亞洲的日本,歐洲的德國、義大利;戰勝國的作品:歐洲的英國、法國,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美國,梭巡詩人的見證。
戰後的台灣並沒有世界性的戰後視野,而是被侷限在既非戰敗國也不是戰勝國的迷障,在外來黨國體制的反共抗俄到反共而不抗俄的國策牢結裡,流於國策文學的教條主義和波蘭詩人米洛舒(C. Milosz, 1911–2004)在〈有贈〉這首詩裡所說的:官方謊言的共謀、喉嚨被割的醉鬼狂歌以及大二女生的讀物,三種不能挽救國家和民族的詩。
一九七○年代,一九八○年代,我多次出任《笠》的主編,以世代論、時代論、藝術論、社會論議題,嘗試重建戰後台灣詩史,幾乎在各期的卷頭言留下篇章。這也是我從詩到詩論的跨越之路,也是後來在論述領域有所發揮的原因。詩,在造型與精神領域,既重形式,也重意涵,對藝術性和社會性有所觀照。從詩論評走向藝術與社會評論,一九八○年代末出版了《做為一個台灣作家》,一九九〇年代初出版《戰後台灣文學反思》之後,應邀在許多報刊撰寫專欄,留下許多從戒嚴走向民主化的見證。
一九八七年七月,台灣宣佈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我正在從美國加州洛杉磯往聖地亞哥的一號公路途中。記得,下車和友人走向太平洋海濱,腦海浮現米洛舒的〈禮物〉,一首隱喻歡喜迎來自由的詩。那時,他仍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他詩裡喻示的「他們的敵人會把自己交付毀滅」(出自〈咒語〉)還未實現。東歐不久自由化了,他是結束流亡約四十年的人生,回到波蘭,並安息於斯。
禮物
米洛舒/著 李敏勇/譯
這麽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做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面。
這世界沒有什麼我想擁有。
沒有任何人值得我羡慕。
我遭受的任何惡禍,我都忘了。
認為我曾經是一樣的人我也不會難為情。
我身上再沒感到痛苦。
挺起身子時,我看到藍色的海和帆。
這首詩寫了一位從東歐國家波蘭流亡的詩人的信念和期待,把自由視為禮物,在祖國重獲自由時,亦即看到藍色的海和帆時,他挺起身子的視野。東歐是二戰後、從納粹德國解放而陷入共產體制的國家,這些國家在戰後的世界詩有突出的表現,米洛舒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的詩讓人看到詩人存在的意義及價值,在困阨的時代不只破滅、希望,而懷有信念。
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台灣筆會成立。參與籌備的我,在起草成立宣言中,以「作家應當是一個精神的政府。作家應當是社會的良心、時代的證人;也應當是心靈的守護神、希望的領航員。作家應當站在人的立場;堅持公理與正義、信守和平與愛、追求善美與真實;透過文學和藝術的創作、評論和研究,透過社會批評丶更透過文化運動,彰顯其意義與價值。」起頭,期勉、召喚台灣作家,追求政治民主化、經濟的合理化丶文化優質化的理想和憧憬,參與社會改造和國家重建。這一年,從蘇聯流亡美國的詩人布洛斯基(J. Brodsky, 1940–1996)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名言:「詩人應當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是深印在我腦海的一句話。
在美、加的一個多月文化之旅,經歷多場演講、朗讀及文學會議,回到台灣後,我決定把自己的人生放在寫作及社會參與,內人麗明不只同意,也協助我。一九八七這一年,我,四十歲,企業職場已穩定。我決定自己的人生要回到文學的初衷,並加上公共事務。籌組四七社(一九○○~二○○○)、擔任台灣筆會會長(一九九三~一九九四)、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一九九九~二○○五)、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一九九八~二○○二)、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二○○一~二○○五),就是我四十歲到近六十歲的投入。一直到二○○七年,我六十歲,意外獲頒國家文藝獎,才回到自許的一個人的文化運動。
積極介入社會的二十年間,也是詩集《傾斜的島》(一九九三)、《心的奏鳴曲》(一九九九)、漢英對照《如果你問起》、漢日對照《思慕與哀愁》兩冊詩集,以及譯讀詩、散文集、評論集、隨筆集、編選詩文集,大約四十本書出版的時期。以詩為主,兼及歌詞、譯讀詩、文學評論、文化評論、社會評論,藝術評論,甚至編選詩文集。這期間,常應邀到世界許多國家的台灣人社團年會演講,朗讀詩。一個台灣詩人的心靈之旅和時代見證,是我那時期的寫照。
研究愛爾蘭文藝復興與獨立運動的英文學者吳潛誠,曾以〈政治陰影籠罩下的詩之景色〉論我的詩集《傾斜的島》,他說:「李敏勇的詩作常涉及政治,但他並不是只要政治,不要詩的作者。相反的,他是一位對於詩之為物持有崇高信念的詩人。」在閱讀李敏勇《心的奏鳴曲》的論述〈擦拭歷史丶沖淡醜惡以及笫三類選擇〉,以愛爾蘭詩人薛摩思.希尼(S. Heaney)如何以詩為受難者清洗傷口?說我越來越著重如何以藝術技巧來舒緩沉重的擔當。這讓我想起德國漢學家馬漢茂(Martin)在波鴻.魯爾大學一位學生有關我詩與論述的研究《認同的探索在台灣──詩人、批評家李敏勇》(一九九六)。他們觀照了我,也讓我省察了自己。
二○○七年,我以「一個人的文化運動」表明從諸多公共事務團體主事者走向個人性參與的心意。進人白秋、玄冬的人生階段,我想以更具個人性的角色,在創作、論述以及社會介入、參與,實踐更純粹的心意。悠忽之間,已過了十多年。回看這段時間,自己各種文類著書大約每年二~四本,累計已有相當數量。自己少小時期走向詩人、作家的專職之路的夢,似乎實現了。之前的詩集,也以《青春腐蝕畫》、《島嶼奏鳴曲》的合集呈現。而通行台語詩集另有《一個台灣詩人的心聲告白》有聲書(一九九六),以及後來的《美麗島詩歌》(二○一二)。
我的詩之志和文學心,經歷《笠》的詩人學校啟蒙,也在當代世界詩譯讀的詩人學校洗禮。詩,相對於文學,就如數學之對於科學。以詩為本,以詩為角色,我在沒有地圖的旅行之途,戮力墾拓耕耘,一邊跌倒,一邊發現。我的意志和感情立基在台灣這塊土地,也放眼世界。獲頒國家文藝獎之後,蔡佩君以《詩的信使──李敏勇》為我書寫了評傳,她的評傳與有關我的研究論文比較起來,顯示更多的生命觀照,是一本文學的傳記,呈現了我在時代變遷中的精神軌跡。
想起我詩集《心的奏鳴曲》裡的兩首詩,那是我的〈備忘錄〉和〈自白書〉,也算是告白與批評:
詩人應許的國度
以樹葉和花繪成旗幟
號角吹出的奏鳴曲代替征戰之歌
因季節的嬗遞憂傷
因歡喜而落淚
愛惜每一個字
為語言剪裁適合的衣裳
──〈備忘錄〉摘抄
我的朋友
以一本詩集為誌
結束詩人生涯
他說
有些詩人
譲人感到羞恥
……
為了詩
我顫慄的舌尖
在意義的黒夜觸探
……
孤獨地仰望星星
面對廣漠世界
我也尋求慰藉
……
詩
其實是
自己面對自己的備忘錄
每一本詩集
都是自白書
向歷史告解
……
──〈自白書〉摘抄
我的詩人之路,起自南台灣的高雄,延伸到中台灣的台中,以至北台灣的台北。我童年成長之地:國境之南、島嶼恆春的屛東,更是英語詩人奧登(W. H. Auden)所說的詩人學校,是有海,有大武山,有美麗田園的自然學校。從鄉村到都市,經歷農業到工業化的社會變遷,更經歷戒嚴專制到民主化、自由化的時代進程。半世紀的光影印記在人生的形跡,譜呈在語言的行句,成為一本一本書冊,鑑照著我的生命史。
《自白書》(二○○九)之後,我的詩集是《一個人孤獨行走》(二○一四)。詩人,終究是孤獨的,孤獨地承擔做為詩人的責任。走向一個人的文化運動,我不再以團體的角色去實踐社會責任,而是以詩人的身分發聲。從詩集延伸的各種文類著作,也都是立基於詩人位置和詩的本質的相關展現。出版《雲的語言》的五十年後,二○一九年,《國家之夢,文化之愛》、《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雙重構造的精神史》、《私の悲傷敍事詩》,分別是社會評論、詩史論及小說,並編集一冊攝影詩文書《自由之路,人權光影》。《李敏勇精選讀本》以文類分輯,是各種著譯作品的選萃,做為我半世紀著述之路的多音交響與多面顯影,並為我詩之志與文學心的呈現。
內容連載
【詩】
遺物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休戰旗一般的君的手絹
使我的淚痕不斷擴大的君的手絹
以彈片的銳利穿戳我心的版圖
從戰地寄來的君的手絹
判決書一般的君的手絹
將我的青春開始腐蝕的君的手絹
以山崩的轟勢埋葬我
慘白了的
君的遺物
我的陷落的乳房的
封條
──一九六九
孤兒
誰都會是孤兒
從河邊的一隻死貓
從街道的一條病狗
從戰場的一具屍體
我悄悄地
收集著成為孤兒的悲哀
像嚥下的貯食
它們輪番出現
期待反芻
我是這樣過活的
從一隻死貓的河邊
從一條病狗的街道
從一具屍體的戰場
我的夢
出發去旅行
誰都會是個孤兒
──一九七一
夢
夜黑以後
現實有一個缺口
我是打那兒
逃亡的
雖然你
像監禁終身飯一樣地
監禁著我的一生
然而
逃亡以後的我
是自由的
你不能捕獲我愛的掌紋
你不能捕獲我恨的足跡
──一九七二
【譯詩】
當我仍然看得見時 日本/田村隆一(一九二三~一九九八)
星星的光
原野的花
海滾滾回來的地平線
陸地倒轉的地平線
有一張臉在帽子下
假使我打開一扇門有人在那兒
一隻鳥的羽毛
一隻小動物的足印
秋天匆匆墜落的夕陽
春天朦朧的月
我曾經寫了
「時間不會死
人會死亡」
我已看過任何年歲的人死亡
而我
也會在人生盡頭死亡
我看得見
但世界之中和我眼睛一樣看見的
只有時間